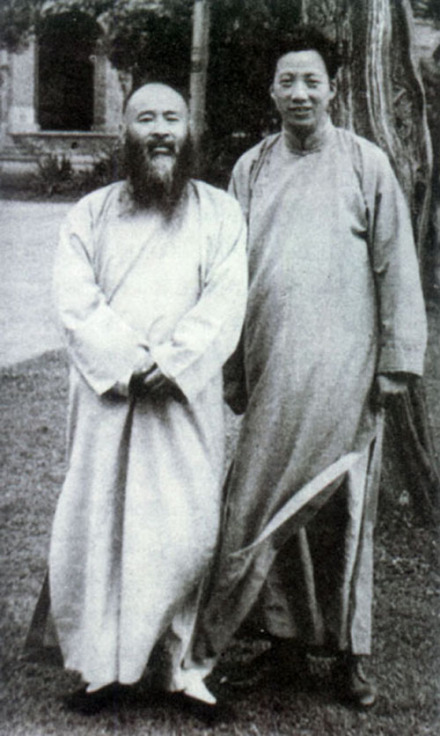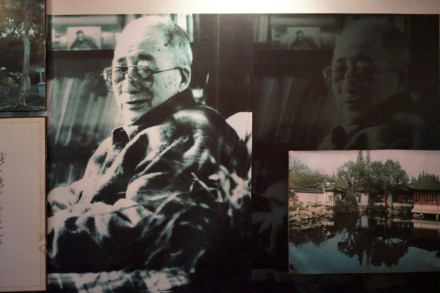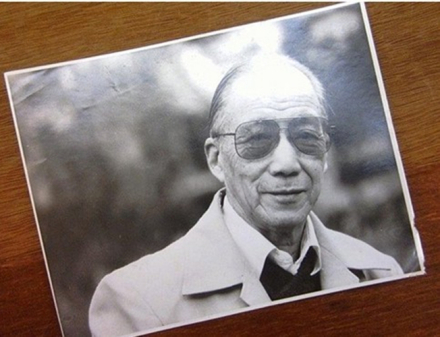-
陈从周 编辑
陈从周(1918年11月27日-2000年3月15日),原名郁文,晚年别号梓室,自称梓翁,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浙江杭州。中国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学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大师,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早年毕业于之江大学文学系。擅长文、史,兼工诗词、绘画。著有《说园》等。
2000年3月15日,陈从周在上海病逝。
陈从周1918年11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童年时期即喜欢养花种草、叠石理水和观察工匠造房起屋,并喜爱绘画,喜背古诗。
1938年,入之江大学文学系中国语文学科。
诗词师承夏承焘教授。1942年毕业后,受聘于杭州省立高级中学,市立师范学校、上海圣约翰附属高中任国文、历史教员,
1944年,与海宁蒋定结婚,蒋定为徐志摩姻兄妹,得悉志摩轶事,开始了对徐志摩的钻研。同时,被著名画家张大千所赏识,成为张大千之入室弟子,攻山水人物花卉。
1948年,在上海首开个人画展,以“一丝柳,一寸柔情”的诗情画意引起画坛的瞩目。
1949年,发表处女作“徐志摩年谱”,成为当今研究徐志摩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宝贵资料。
古建筑园林艺术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积极从事保护、发掘古建筑工作。他揉中国文史哲艺与古建园林于一炉,出版了第一本研究苏州园林的专著,其《说园》五篇,总结了中国园林的理论。
晚年参加多处园林设计实践,直接参与指导了上海、浙江诸多古园的维修和设计工作。
1950年,任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副教授,教授中国美术史,结识古建筑专家刘敦桢教授,开始了陈从周教授的古建筑生涯。同年秋,执教于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正式教授中国建筑史。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从周受到了迫害,
1971年,下放皖南干校,1972年,开始参与连云港海青寺塔修理工程,
1974年,指导阿尔巴尼亚进修教师。考察了济南、曲阜、泰安、聊城地区的古建筑,为保存聊城明初光岳楼大木结构做出重要贡献。
1975年,在极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著述《梓室余墨》40余万字,详细记述了一生中的交往、研究、各地山川风光、民俗、民情、遗闻轶事。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陈从周绝处逢生。多年积压在心头的话,一下子爆发出来,这就是《说园》的第一篇,对古建筑、古园林的正确评价和多年破坏的无情抨击,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说园》五篇情真意切,融文史哲艺与园林建筑于一炉,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纷纷出版不同版本、译本,前后有英文译本、日文译本,以及德文、法文、意文本。
1978年,将苏州园林局部模制,输出至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即明轩,成为新中国以来园林文化建筑对外输出之先河。贝聿铭雅嘱他写就长卷水墨丹青《名园青霄图卷》,复请国内文化耆宿、书法名家题咏,现存纽约贝氏园,成为一件极为珍贵的书画名品。
1980年秋,首次指导日本来华研究学者关口欣也博士。为适应全国各地的旅游热,修复名胜古迹热,提出“还我自然”、“文化旅游”、“先绿后园”、“绿文化”等响亮口号,针对社会上的“一切向钱看”倾向,提出“梓翁画图不要钱”,“一文不取,敞开供应”,学校教师应是“万卷户”等。到处演讲报告,所到之处极受领导、群众的欢迎和接待。
陈从周的咏西湖诗,饱含着对西湖建设的关注。他写有《应杭州园林局邀游西湖赋赠诸公》一诗,因西湖游人如织,摩肩接踵,他在诗中提出:“切望南湖多着眼,园林聚散理寻常。”主张开发西湖南线景区,使游人聚而能散,这是很有前瞻性的见解,意见很快地被杭州市园林部门所接受,接着南线景点大开发,而且各景点不收门票,开了全国游览免费的先河,如今南线景区游人已超过昔日爆满的北线景区。
陈从周与我谈起西湖建设时说:“改园更比改诗难。”他有时谈起杭州的园林建筑感慨真还不少,有一新落成的大饭店请他题词,他写了“明望一碧眼中收”,饭店员工尽朝他鼓掌,竟看不出其中的深意,他是有讽刺意思的,饭店造在西湖边上,为什么又造得那么高,太高了破坏西湖的景观。
他还多次谈到,在过去,对西湖景点命名,很讲究声韵平仄,如“三潭印月”,就是平平仄仄,“断桥残雪”也是平平仄仄,读起来琅琅上口,有的景名很有诗情画意,如“双峰插云”、“南屏晚钟”,有虚有实,情景交融,虽为人作,宛是天开。陈从周对杭州人文历史的熟稔,决不逊于那些“杭州通”们,一些名人故居,他了如指掌,而且还是一本“活家谱”。
他认为中国造园的立意构思大多出于诗文、额联,点缀和题咏园林景色,所以园实文,文实园。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园林是融入历代文人气质的自然景观,讲究自然,他有诗云:“村茶未必逊醇酒,说景如何欲两全;莫把浓装欺淡抹,杭州人自爱天然。”杭州建设千万不能继承不足,革新太快,要有中国特色,如果让西湖穿上“西装”那就不伦不类了。
“惆怅滇池唯一角”
昆明滇池是个好去处:金马、碧鸡二山东西夹峙,池上烟波浩渺,一碧万顷,风帆点点,景致极佳。池周多名山胜景,有大观楼、西山、海埂、白鱼口、郑和公园、石寨山古墓群遗址等。有客轮行驶于西山、白鱼口和海口之间。
那天,陈从周在昆明旅游局、园文局有关领导的陪同下游览,兴致极高,最后应邀参加滇池之畔一个高级宾馆的落成典礼,宾馆大门口彩旗飘扬,乐队高奏一曲又一曲的迎宾曲,素有“照相式记忆”之称的陈从周,仔细看了看滇池的一角,禁不住问陪同人员:“这宾馆的地基原来也是滇池的吗?”当被告知正是被填平的滇池一角后,陈从周的雅兴大减,正如他事后诗中提到的“惆怅滇池唯一角,大观楼下独徘徊”,甚至还写过一篇《滇池虽好莫回来》的文章,从诗文中可知陈从周当时心境很差。他在文中说:“大观楼前的景色仿佛西湖三潭印月的一个侧面,五百里滇池,水的面积破坏得太惨痛了,将来要被人笑的,到时后悔来不及了。”
典礼很隆重,有关部门再三恳请陈从周题词留念,陈从周踌躇再三,在一张展开的宣纸上,大写了“回头是岸”,在场人不解其意,只知出自名家手笔,当属殊荣,总经理连连向陈从周鞠躬致谢,四周掌声不断。
陈从周每每忆及此事,感慨万千:“哪能一切向钱看,我写‘回头是岸’,潜台词是滇池再这样填下去必将是‘苦海无边’,破坏生态平衡,乱建筑,必遭大自然的报复,将子孙饭提前吃了,到时后悔也不行了。”
陈从周的话说得很对!以后看到新华社发了电 讯稿,谈到由于滇池四周不少地方被填平,滇池水面积减少了,违法建筑多了,水质变坏,破坏了生态环境。有识之士呼吁,要恢复滇池的原貌,可造成的损失,已是无法估量。这段弯路走得太不应该了。
“大饼教授”的呼吁
晚年的陈从周对名利看得很淡,从他制作的名片中就可以看出来,只具姓名、家庭地址及电话号码,什么“中国建筑史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美国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顾问”等,全都消失了。
陈从周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却给后人留下很多宝贵的东西。在这些遗著的每一页里都浸透了他的心血,浸透了他对我们华夏民族文明的热爱和真切的感情。
潜心地细细阅读这些遗著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渐渐地沉醉到那些字里行间中去,尽情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浓郁与香淳,充分地领略中国古代建筑和园林的景境之神韵。
正如叶圣陶先生在关于《说园》的一封书信中所说“从周兄熔哲文美术于一炉,以论造园,臻此高境,钦悦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