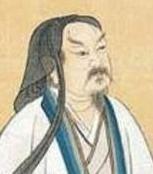-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编辑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五言组诗。这两首诗都是即景抒怀之作。第一首反复陈说被阻穷湖、急切不能到家的苦恼;第二首进而感叹行役之苦,并借眼前自然景象暗喻仕途的风波险恶,曲折地抒发厌倦官场、怀恋清静自在的田园生活的情思。第一首以叙事起兴,第二首以议论开篇。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1
其一
行行循归路2,计日望旧居3。
一欣侍温颜4,再喜见友于5。
鼓棹路崎曲6,指景限西隅7。
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8。
凯风负我心9,戢楪守穷湖10。
高莽眇无界11,夏木独森疏12。
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13。
延目识南岭14,空叹将焉如15!
其二
自古叹行役16,我今始知之。
山川一何旷17,巽坎难与期18。
崩浪聒天响19,长风无息时。
久游恋所生20,如何淹在兹21。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22。
当年讵有几23?纵心复何疑24!
词句注释
庚子岁:晋安帝隆安四年。规林:地名,今地不详。
鼓棹(zhào):划船。棹:摇船的甲具。崎曲:同“崎岖”,本指地面高低不平的样子,这里用以比喻处境困难,《史记·燕召公世家):“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
指:顾。景:日光,指太阳。限西隅(yǘ):悬在西边天际,指太阳即将落山。限:停止。隅:边远的地方。
归子:回家的人,作者自指。念:担忧。前涂:前路,指回家的路程。涂同“途”。
凯风:南风,《尔雅·释天》:“南风谓之凯风。”负我心:违背我的心愿。
戢(jí):收藏,收敛。枻(yì):短桨。穷:谓偏远。
高莽:高深茂密的草丛。眇:通“渺”,辽远。无界:无边。
独:特别,此处有挺拔的意思。森疏:繁茂扶疏。
瞻:望。百里余:指离家的距离。
延目:放眼远望,“南岭:指庐山。诗人的家在庐山脚下。
将:当。焉如:何往。这首诗慨叹行役之苦,思念美好的田园,因而决心辞却仕途的艰辛,趁着壮年及时归隐。
一何:多么。旷:空阔。
巽(xùn)坎:《周易》中的两个卦名,巽代表风,坎代表水。这里借指风浪。难与期:难以预料。与:符合。
崩浪:滔天巨浪。聒(guó)天响:响声震天。聒:喧扰。长风:大风。
淹:滞留。兹:此,这里,指规林。
人间:这里指世俗官场。良:实在。
纵心:放纵情怀,不受约束。
白话译文
其一
归途漫漫行不止,计算日头盼家园。
将奉慈母我欣欢,还喜能见兄弟面。
摇船荡桨路艰难。眼见夕阳落西山。
江山难道不险峻?游子归心急似箭。
南风违背我心愿,收起船桨困湖边。
草丛深密望无际,夏木挺拔枝叶繁。
谁说归舟离家远?百余里地在眼前。
纵目远眺识庐山,空叹无奈行路难!
其二
自古悲叹行役苦,我今亲历方知之。
天地山川多广阔,难料风浪骤然起。
滔滔巨浪震天响,大风猛吹不停止。
游宦日久念故土,为何滞留身在此!
默想家中园林好,世俗官场当告辞。
人生壮年能多久?放纵情怀不犹疑!
此诗写于东晋隆安四年(400年),作者陶渊明三十六岁。作者此时在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府中任职。此前,陶渊明奉桓玄之命出使京都建康(今南京市),完成使命后,返途中路过江西,准备顺道回家省亲,然而被风阻在途中。这两首诗就是写在途中受阻时的情景。
整体赏析
其一
第一首诗总的调子是抑郁的,但前四句并不沉闷,抑郁中有欢快,泪与笑俱,起伏多变。“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归心似箭,匆忙赶路,心里计算着到家的日子。为了表达归家的急迫心情,诗人注意了词语的选择,“行行”是重言,富有表达力,写出了诗人奔走不停的祥子;“计日望旧居”的“计”和“望”,准确而形象地反映出诗人归家途中的心理活动,诗人很想回到自己久别了的“旧居”,去看望自己的亲人,他唱道:“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在行役路上动乡关之思,盼与家人团聚,这是人之常情,陶渊明用诗的语言道出了这种人之常情,最容易引起共鸣。
“计日望旧居”的陶渊明不希望在路上停留。然而,偏偏行船遇风,被迫在穷湖停船,这当然使他苦恼。离家只有百余里,却回不去,他只好遥望南岭,对空长叹,心情是无可奈何的。诗人不仅写了这种欲归不得的苦恼,他还借叹行役的机会表示了对官场的厌倦,对仕途的忧惧,对怀才不遇的抗议。有了这些内容,就看见了诗人的心,感觉到了他跳动的脉搏。
在表现这些内容的时候,诗人没有直说,而是含蓄地表现出来,为了诗意的含蓄,诗人采用了三种手法。一种是借景抒情,借景达意,字面上是写景,字里行间却藏着诗人的寓意,“言在此而意在彼”。“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从字面看,这不过是诗人在叹“行路难”,在埋怨日落黄昏夜幕降临得太早;透过字面,便不难发现,诗人是在借助眼前的景物流露自己对官宦生活的厌倦情绪。他怨天恨地,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在他的眼里,江南夏日的风光也变得那么荒凉,那么可怕,没有欢乐的情绪:“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扶疏”。不是风光不美,而是诗人的情绪不佳。诗人不去赞美行役途中的风光,正说明他想结束劳累的行役生活,想离开讨厌的官场。
另一种是用双关语达意。“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字面是说行路难,征途艰险可畏,可实际是说官场多风险,吉凶难料。当时,东晋王朝岌岌可危,孙恩在浙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逐渐逼近京师,陶渊明的上司桓玄屡次上表要求讨伐孙恩。王室腐败,义军攘起,军阀桓玄又野心勃勃,社会极具动乱,想到这些诗人不能不瞻“念前涂”。由此看来,诗人笔下的“江山”,决不仅指自然界的山川,而是指国家社稷,“前涂”也不仅仅是指征途,而且是指诗人自己在社会动乱时的仕宦前途。“江山”和“前涂”都是一语双关,值得玩味。
除了上两种,诗人还使用了隐喻的手法。“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这两句是说风不从人愿,阻延归期。其实,诗人的命意远不止于此,他一连用了三个隐喻,来描述自己怀才不遇的处境。“凯风”是可恨的,它与诗人的心相违;凯风在这里暗指压制陶渊明的世族权贵。“戢枻”是可叹的,因为“枻”的作用在于划船,当“枻”被“戢”起来以后,就失去作用了。“穷湖”是荒凉的地方,船泊穷湖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者陶渊明是有才干的,然而,他只能在桓玄手下当幕僚,而且还要行役千里,致使自己无所作为。桓玄的慕府就如同“穷湖”,陶渊明发出“戢枻守穷湖”的叹息是很自然的,并非无病呻吟。
最后,诗人慨叹只有百里之远,因风受阻,不能及早返回旧居,发出了“将焉如”的叹息,但只不过是空叹而已,与前面的“归子念前涂”一句联系起来看,这几句诗真实地抒写了诗人“出仕”与“归隐”的矛盾痛苦心情。
从全诗看,首尾两部份的抒情基本上是采用直说的方法,感情真挚热烈。诗的中间部份则采用借景达意、一语双关和隐喻的方法,表现出诗人的隐衷,富有意趣。
其二
与第一首诗相比,第二首诗写得更精炼一些,全诗仅十二句,集中表达了陶渊明厌倦仕途、依恋田园的思想感情。第二首诗是真实动人的述怀诗。诗人对做官不感兴趣,下决心要辞别官场。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做官有行役之劳,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尤其苦。所以陶渊明得出结论说:“自古叹行役”。然而,行役者究竟有些什么可叹的苦,陶渊明以往并无切身体验。可当他为桓玄当差,奔波于建康和江陵之间,不远千理,其间的艰难险阻可以说是“备尝之矣”,所以他感慨道:“我今始知之”。这里,言未尽意,诗人的心里是在说:行役当差的苦头我尝够了,谁还想迷恋仕途。
陶渊明厌倦仕途的另一个原因是,仕途多风险,吉凶难料。在诗人看来,做官是一种危险的事情,倒不如及早告别官场。为了表达这个意思,诗人并未直说,而是借景言情,引用典故达意。行役途中,面对山川荒野,诗人的心境是孤独而悲凉的,发出了“山川一何旷”的感叹。这不是对山川秀色的赞美,而是对山川旷野的畏惧。由于心情的关系,大自然在诗人的眼里也是可怕的。诗人借山川之险来陪衬仕途之险,意在说明仕途可畏,潜藏着祸福风云。何时为福,何时为祸,谁也不知,“巽坎难与期”。用“巽坎”来比喻仕途中的吉凶顺逆,是十分恰当的。“崩浪贴天响,长风无息时”。这是全诗的秀句,写出了诗人在行役途中对山川风物的真实感受。诗人的用词准确,而又很会夸张。他不说“巨浪”,而说“崩浪”。一个“崩”字,不仅有形象,而且有声音,绘声绘色。“聒”字准确地形容出巨浪咆哮时的杂乱之声。“崩”字形容声大,“聒”字形容声杂。诗人借自然景象来描绘官场内部的激烈斗争,像崩浪震天那样可怕。
宦游之人长年在外,离乡背井,这在感情上是一种痛苦。陶渊明也经历着这种痛苦,行役途中他格外思亲。“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这是陶渊明的心声,抒发了思亲的感情,悔恨自己不应该误入仕途,更不应该在仕途淹留。有了这悔恨之后,诗人便下定了决心,要罢官归田。这里,可以看见陶渊明的内心世界,他赞美园林,鄙弃官场。诗的结尾“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表面似乎是消极情绪的表露。其实,诗人并未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他是在思想痛苦的时候才这样写的,是一种愤慨之言。诗人正当壮年,大志未展,繁杂的公务消磨着他的年华,而且受着官场的牵制约束,俯仰由人,他想摆脱官场的牵制,回到园林,使自己的身心得到自由。诗人盼望有“纵心”的时刻,这不是要放纵自己,而是要做一个自由人。不贪富贵,纵心归田,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这是陶渊明真实的思想。
名家评价
明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二首专写归省,恨处急处,足催唤世间游子。(其一“行行循归路”)崎曲怨地,限隅怨日,凯负怨风,森疏怨木,层层添苦。路直则归速,日长则行倍,地不可缩,日不可击,此无可如何者也。风若顺而何忧路曲,何忧日短,木不森则无所蔽。远望可以当归,路曲尚藉目直,日短难抑心长,乃两受阻焉,此偏添相挠者也。写怨幻奥。
清吴菘《论陶》:“计日望旧居”,写尽客子情态。前四句皆志喜,后皆叹也。路曲景限,江山又险,已为可叹。乃风又负我。又穷我,远则高莽悬邈,近则夏木蔽亏。百里非遥,瞻望弗及,与前“计日”殊相左矣,能不永叹。
清吴瞻泰《陶诗汇注》卷三:此诗为归省而作。一片游子思归真情,急于到家,偏为风阻,触目生怨,觉路为之曲,目为之限,夏木为之蔽,使千载而下,犹觉至情流露。曰“计日望旧居”,曰“延目识南岭”,近见乡关,首尾遥对。
清方宗诚《陶诗真注》:观渊明此诗及《孟府君传》,所用《凯风》皆指母言。可知古训《凯风》,非母不安其 室之诗也。如《凯风》为母不安其室而作,渊明岂敢引用,以况己之母哉!
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指景”句琢,非琢词,乃琢意耳。结四语有作意。通首俱尖仍,惟笔老故不佻。
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余读“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及“久游恋所生”,与夫《悲从弟》、《祭程氏妹》诸诗文,而知公之真孝友;读《贵子》、《告俨等疏》,及“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等句,而知公之真慈爱,自古未有居家不尽孝弟慈三者而能为国之忠臣者也。
清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三:杜少陵诗中字法多脱胎于此。“戢枻”、“崩浪”等句,写阻风警动。“谁言”、“久游”等句,叙归省意切。
明何孟春《陶靖简集》卷三:(其二“自古叹行役”)朱子尝书此诗与一士子云:能参得此一诗透,则今日所谓掣业,与夫他日所谓功名富贵者,皆不必经心可也。
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陶渊明一生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28岁以前,由于父亲早死,他从少年时代就处于生活贫困之中。第二时期,学仕时期,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41岁。第三时期,归田时期,从义熙二年(406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病故。归田后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田园诗一体。陶诗的艺术成就从唐代开始受到推崇,甚至被当作是“为诗之根本准则”。传世作品共有诗125首,文12篇,后人编为《陶渊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