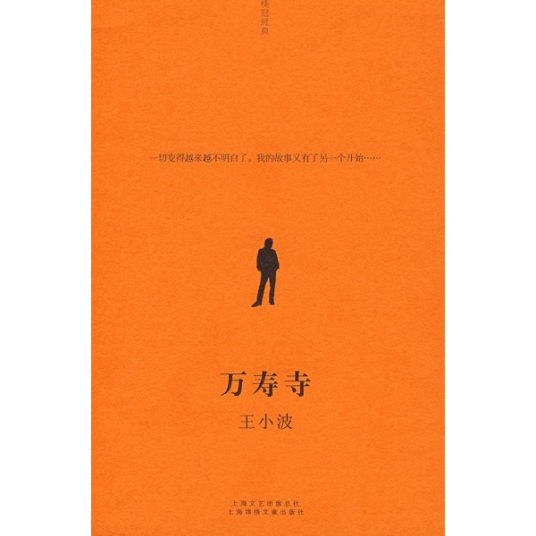-
万寿寺 编辑
《万寿寺》是作家王小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收录于小说集《青铜时代》中,首次出版于1997年5月。
《万寿寺》中有两个主人公、两条线索,各自在不同的时空中发展着自己的故事,有时候也交替发展。 《万寿寺》中有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人物王二,他在寻找自己因为车祸失去的记忆;与此参差进行的是他同时在阅读并续写着一个古代的故事——薛嵩和红线等人在湘西凤凰寨发生的故事。
王小波在这部小说里打破了传统小说情节的线型叙事解构,使用了现代手法,时空错乱和从几种不同假设开头的“并行叙事”,使得他的叙事完全脱离了叙事规则。
全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至三章是第一部分,讲述“我”失忆前写成的手稿中薛嵩和红线经历的事情。第二部分从第四章到第七章,这一阶段,“我”回忆起自己的作者身份,并对原手稿进行更深层地挖掘和解构。第三部分是第八章,讲述理想人物在理想的长安城中与现实人物在现实的北京城中的反差。这一部分是对前两部分的总结和深化,“我”追求“诗意的世界”的理想和毫无诗意可言的现实使“我”苦闷、绝望,在眼看一切都无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后开始努力寻找出路。
薛嵩
晚唐时节,薛嵩离开长安,带了一些雇佣兵和一老一小两个妓女来到湘西,建了一座凤凰寨;后来,薛嵩抢了苗女红线做老婆,并遭到老妓女雇来的刺客的袭击,薛嵩射死了老妓女,还有可能射死小妓女,由于红线捣乱,没有射中。
王二
现代故事开始时,王二处于失忆的状态,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和过去,凭借一张没有名字的工作证,他来到万寿寺一间办公室里,办公桌上有一叠稿纸,写的是薛嵩的故事,第二天王二开始对薛嵩的故事进行重写。七、八天后,他找回了自己的名字、身份和失去的记忆。但寻回的记忆并不像《追忆似水年华》里那样带给普鲁斯特至福的时刻,而是成为被王二拒绝的异化之物。因为失去的记忆正是王二无法逃脱的命运:王二是设在万寿寺里一个文史机构的职员,被困在万寿寺象征的命运之圈里,无法逃避地成为时间和庸俗的猎物。
作品主题
王小波在小说《万寿寺》中拒斥道德训诫,向虚伪做作的礼教与平庸鄙俗的世风投去轻蔑的眼神。小说中动辄便以道德训诫律己律人的人物均遭到他辛辣的讽刺,如最初的手稿中的薛嵩、老妓女、塔中的老虔婆等人。若具体说来,王小波反道德论的唯关主义创作意识在小说中主要两个方面:一是对裸体的崇尚,二是对性的高扬。
小说中的主人公王二和薛嵩都追求个性、热爱自由,都想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观进行生活,他们都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想在现实而且保持自己精神上的独立,在主人公的身上反映出作者对自由精神追求。
艺术特色
《万寿寺》里有一个关于薛嵩和红线的故事手稿,其中只讲述了一个故事,但却讲述了二十二遍,每次叙述从方式到内容都迥然相异,又隐约相关,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关系设置、情节发展、逻辑因果一次又一次地被创造,而后被颠覆,再创造,再颠覆,薛嵩建寨,薛嵩成人.薛嵩抢亲,刺客来犯,黄蜂退敌,宝塔救女……这些故事场景被一次又一次地描写;薛嵩、红线、雇佣兵、老妓女、小妓女、刺客(们)……这些人物幽灵般出没于叙述的迷宫,性格随着时间、地点、环境、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即令生死大事也随着各种情节因素的编排组合而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对于读者而言,面对《万寿寺》一切都扑朔迷离、无从捉摸,一切情感态度、道德判断、价值理念都被悬置,甚至被抛入明暗之间的尴尬境地,读者也失去了自身的定位。这就是王小波试图在小说《万寿寺》中想要做的事:穷尽可能性。
《万寿寺》的叙事结构纷繁复杂,但其情节线索可以概括为王二出院后试图恢复记忆、找寻自我的过程。在这一周的时间里,他借助自己的手稿找寻精神自我,在真实生活中通过提示寻回现实记忆。很明显,《万寿寺》中讲述的“我”出院后的生活为故事事件,生成于第一叙事中;“我”在手稿中讲述的是元故事事件,生成于第二叙事中中。按照在手稿中出现的时问先后,这四个元故事事件分别为:A、失去记忆之前写的关于薛松和红线在湘西的故事;B、出院以后恢复记忆过程中改写的薛松和红线在湘西的故事;C、出院后恢复记忆过程中写的薛松在长安里的故事;D、出院后恢复记忆过程中写的长安城中“我”的故事。这四个元故事事件是文本的主要表现对象,每个元故事事件都有一个主要的线索,后从中蔓生出许多枝权:或是将情节开头解构成多个“开始”,或是将一个功能解构为多种原因和多种可能性,或是取消叙事时问、只描述场景式的想象。
《万寿寺》不以线性的时间为核心背景来填充情节,而是以叙述者的思维和意识为核心来定义和关照时间。时间被内化为若有若无的要素融入到“我”的意识流动中,以心理时间取代线性时间,整体上表现出空间化。
“我”的故事发生在当代,薛嵩的故事发生在晚唐时期,作者并不是对这两个叙述单元作边界清晰的独立呈现,而是在古今(薛嵩的故事和“我”自己的故事)、外叙述层和内叙述层之间、想象和现实之间自由穿梭,时而是王二,时而是薛嵩、红线或妓女。除了暗示读者第一叙事中故事的时问幅度为一周以及出院后第一天的时问可以再现之外,文本中其他地方的时间(如简单的“早上”“中午”“傍晚”)都很难定位,仿佛只是不同时间矢向中的任意一点;而古今的自由对话则将历史内化为一种共时性的结构因素,时间的线性矢量被打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