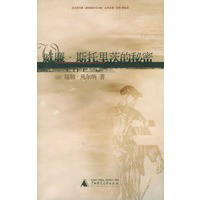-
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 编辑
《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Le Secret de Wilhelm Storitz)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全书共十九章。在凡尔纳去世后曾由其子米歇尔·凡尔纳改写后作为遗著出版。米歇尔·凡尔纳修改版详见“隐身新娘”词条。凡尔纳原稿于1985年首次出版。
威廉·斯托里茨向拉兹城名门闺秀米拉·罗德里什求婚未成,便利用其父留下的隐身术肆意阴挠和破坏米拉小姐与马克的婚事:先是将米拉与马克的婚姻告示撕掉;又在订婚晚会上高唱德国国歌、撕毁订婚鲜花、拿走新娘花冠;最后又当他们在教堂中举行婚礼时,大闹教堂。而米拉则当场昏倒在马克怀中……
干完这些后,斯托里茨又公然向全城居民挑衅,还将神志不清的米拉隐身。
后来,作恶多端的斯托里茨死在复仇的刀下,他的仆人死于心脏破裂。隐身的秘密也永远地埋在了他们的坟墓中。
而美丽善良的米拉小姐却永远只能过着隐身的生活了。
这部小说展示了凡尔纳才华中不为人熟悉的一面,也集中体现了作者关于艺术的伤感见解:艺术作品只有在其模特儿消失之后才算完成。
1897年,或许凡尔纳读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关于《隐身人》的分析文章,然后想象出一个截然不同的“隐身的新娘”——起先是用这个过于明确的题目作为小说名。这两个故事的风格各有不同:威尔斯的作品粗犷,凡尔纳的小说伤怀。不久,大约在1901年,作家重新修改了小说的初稿,使它更朴实、更简洁。
凡尔纳珍视自己的新杰作,但由于害怕埃泽尔反对,所以没敢寄给他。他多次谈到此事,直到1904年9月才下决心,他对埃泽尔说:
《撒哈拉沙漠的大海》、《大海入侵》封笔之后,将有《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完稿,每部小说一卷,我希望有生之年看到它们问世。
出版商对这个问题犹豫不决,准备在出版之前先把它刊登在一份成人版的报纸而不是面向青少年的《教育杂志》上。1905年3月5日,作家终于在辞世前十九天把已杀青并准备付印的手稿交给了出版商,并作了一些说明:
《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一书写的是隐身人,这是道地的霍夫曼风格,霍夫曼恐怕也不敢这样写。对于《教育杂志》而言,或许要一个温和的过渡,改书名也可以是“隐身的新娘”。
儒勒·凡尔纳去世后,埃泽尔读了这部小说。小说的文笔力度、现代情节、激情描写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浪漫令他反感,因而他拒绝出版《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直到1909年,在儒勒·凡尔纳的其他遗作均已出版,米歇尔·凡尔纳按照埃泽尔的要求进行修改之后,《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方才面世。
隐身的题材在儒勒·凡尔纳的著作中是常见的。如在《喀尔巴阡古堡》——另一本言情小说,是在它之后出版的《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一书的孪生兄弟——中已经出现一个消失的女子的幽灵拉·斯蒂亚,但也有(按菲利普·朗托尼的说法)“各种人物,他们或是在行动,但人们永远看不见,或是秘密在行动(如隐身的船长哈特拉斯),或如同看不见的威胁(《美丽的地下世界》中的西尔法克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中的王),或作为隐身的保护人(《美丽的地下世界》中的内尔和《神秘岛》中的尼摩)”。
《桑道夫伯爵》中桑道夫的话语也许能让我们读懂这部小说:“死亡并不消灭人,只是使人变得看不见。”一个消失了的被爱着的女人——就像儒勒·凡尔纳爱过的女人那样——在记忆中总是像“青春洋溢、优雅美丽”的米拉·罗德里什那样美丽和令人难忘。凡尔纳得出结论:“她是家中的灵魂,如灵魂般不为人所见!”马克·维达尔画的光彩夺目的米拉肖像保持着她的纯真,与奥托·斯托里茨照片中的凶相形成对照。再凡尔纳的作品中,同米拉一样的女主人公并不少——与某些预断相反,即使有些人的命运不为人知,但她们不是疯了就是消失了。
这部小说也许可以用“斯托里茨的痴心妄想”为标题,因为他的秘密只要是发泄他对米拉的排他而又顽固的痴心妄想。这种火辣辣、自私、罪恶的妄想,将使那些只把凡尔纳看作以导游身份陪同主人公游览的地理学家的人惊愕不已。亨利·维达尔在匈牙利旅行的感触与监护人埃泽尔定力的道德规范差距甚远。当读者发现威廉·斯托里茨犯下的恶毒罪行时,就不难理解出版商反感的原因了。
当米歇尔·凡尔纳着手改动《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时,他感受到了小说的力量,并不愿毁掉它。1909年9月,他对埃泽尔说:
关于《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我已花了不少时间考虑,尚未决定动笔。……最后,我打定主意保持原样不作任何修改。此书具有的优点比我所能带给它的更大,而至于它的缺点,那是无法纠正的。因此,我的任务将仅限于修饰您向我指出的那几点,并在表现形式上作些修改。
不幸的是,米歇尔·凡尔纳这种清醒的判断遭到了埃泽尔的反对。埃泽尔要求把故事发生的时间从19世纪移到17世纪,也许是——在他看来!——为了使故事更加“可信”。在这荒谬的改动中,米歇尔·凡尔纳删去了各式各样不合时宜的事物和习俗。作家的儿子只会删除,不会添加替换的内容,因此使故事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变得枯燥无味。不再有铁路、轮船、非宗教婚礼、黑色的礼服,不再提及霍夫曼等等。
不久,米歇尔·凡尔纳向出版商指出其想法荒谬可笑:
关于《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这本书,您希望改变小说的“时间”,这是件大事,对此,我从未看出,现在也没有看出什么大的意义。不过,我已顺利地按照您的想法完全改写了这本书,并清除了所有现代词汇,如公里、克、法郎、邮递员等等。也许还有一些!
实际上,剩下的难道只有华尔兹和玛祖卡舞吗?
米歇尔随意修改,挥洒不适宜的感想,例如修改版第二章中的一些内容:
我一开始就夸耀这次旅行奇特,那么,读者——就算有朝一日我会有读者吧!——是否会因旅行的平淡无奇感到惊讶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让他耐心点吧。不用多少时间,稀奇古怪的东西要多少就会有多少。
由于米歇尔不信仰宗教,所以删去了所有宗教的暗示,例如大逆不道地毁坏圣体的那一段:
老司祭手中的圣体饼被夺走了……这个化为肉身的圣子的象征被一只亵渎圣物的手夺走了!然后,被撕碎,碎片飞过祭坛……
这些足以使信奉天主教的读者恐惧!而米歇尔则用一个顽童的恶作剧——结婚戒指被扔出,“飞过教堂中殿”,来代替亵渎圣物这一幕。这位作家的独生子不知道,在一个没有天主回应的教堂里发生这种袭击事件可加剧恐慌,可表现出其父对宗教的疑惑。他父亲曾以讥讽的口吻肯定地说过:“……这种捣乱是不可能在教堂里进行的。难道魔鬼的淫威还能越过上帝圣殿的门槛吗?”
然而,最严重的篡改是:米歇尔·凡尔纳让米拉重新显了身。儒勒·凡尔纳在这部小说——登峰造极的绝笔中,传达了最后的信息:这部艺术作品——描述的画面和这次“奇特的旅行”——表现的是象征着永恒的现实。作品中的人物为活跃情节而牺牲自己的一切。米歇尔·凡尔纳无法理解这层深刻的含义,没有感觉到米拉在场/不在场所富有的诗意,于是选择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这回他对文学犯下了亵渎之罪。
现在大家都知道,儒勒·凡尔纳曾因自己最喜爱的女教师亡故而痛苦。他把女教师的死亡与他失去的初恋密切联系在一起。她就是夺走他年轻时的恋情、后又同别人违心地结了婚的埃尔米尼。在凡尔纳的作品中总有一些面对获胜的情敌而心碎的男人。一位评论家甚至给这种“埃尔米尼情结”下了定义。
在让-皮埃尔·比科看来,女主角们的命运都是悲惨的:
《美丽的地下世界》中的埃朗被人当作鬼怪,实际上她是疯了;《蒸汽屋》中的洛朗斯,人们以为她死了,结果她也是疯了;《喀尔巴阡古堡》中的拉·斯蒂亚,人们以为她疯了,结果她死了;还有米拉,人们以为她失踪了,而她却被隐身了。
虽然魂牵梦绕、摆脱不开的是同一个主题,但各种各样的情节发展却令人吃惊。在其最后一本代表作《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中,凡尔纳同样表现出他临终的恐惧,只是在想起他的“爱捷丽”(罗马神话中曾启示过罗马王尼马的仙女)时才会有所减轻。他的“爱捷丽”具有永恒的影响,虽然所有的人都看不见她,但却活在他心里。艺术作品的生命战胜了死亡,正如爱伦·坡在凡尔纳的灵感源泉《椭圆形画像》中表述的那样。在《蒙娜丽莎》中,年轻的作家就已经懂得:一部“艺术作品只有在其模特儿消失之后才算完成”。在坡的故事中,画家对自己的画像赞叹不绝:“确实,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在《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中,马克·维达尔在米拉的肖像前惊呼:“……比她本人更像!……我觉得这幅画像要活起来了……”
这就是他永远保存的深深的思念,因为在写完《蒙娜丽莎》几年之后,在1874年,凡尔纳还为他在亚眠学院的同事们朗读过这部小说。
坡的故事主角“突然转身看心上人——她已经死了!”,马克·维达尔也失去了妻子,因为她隐身了,但是,在肖像中,她仍然可见到。“你们看见我就像我看见自己一样!”永远美丽的她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