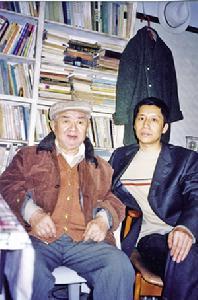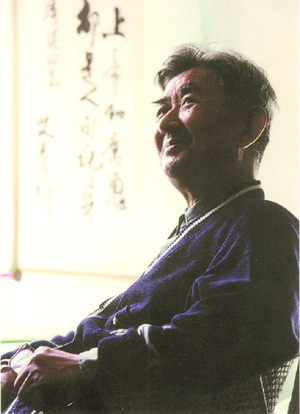-
唐湜 编辑
唐湜(1920年-2005年),原名唐扬和,出版的诗集有《骚动的城》《飞扬的歌》和历史叙事诗《海陵王》等。九叶派在新时期创作产量最大的一位,在九叶诗派中的身份是双重的,不仅是诗人,而且是最重要的诗评家之一。
1920年生于温州杨府山途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曾是小学校长。1943年考取浙江大学外文系,开始真正的诗艺探索。1946年他在上海认识了杭约赫和陈敬容,后来参与《诗创造》的一些编辑工作,经常往来于上海和杭州。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五十年代在北京的《戏剧报》工作,1958年被错划右派,1961年从北大荒回到温州,先在永嘉昆剧团作临时编剧,文革期间在温州房管局下属的一个修建队干体力活,期间笔耕不辍。后来供职于温州市文化局下属的艺术研究所。2005年1月28日下午,在温州逝世。至此,“九叶诗派”仅剩下郑敏。
历任上海星群出版社、《诗创造》杂志编辑,温州师范、温州二中、上海中学教师,《戏剧报》编辑,温州地区文化局、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协浙江分会理事,温州市政协委员。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唐湜是一个不大被人提及的名字,但他确实是一位有才华的批评家,他在批评上极有抱负:“我那时企慕着刘西渭先生的翩然风度,胡风先生的沉雄气魄与钱钟书先生的修养,但我更企望在他们之间有一次浑然的合流。”应该说唐湜曾非常接近这一目标。钱钟书先生曾称赞唐湜的批评“能继刘西渭先生的《咀华》而起,而有‘青出于蓝’之概!”唐湜正式登上评坛是在1947年。这一年,《文艺复兴》杂志3卷1期发表了唐湜的批评文章《伍子胥》。文章认为:“在中国的古老传说里,伍子胥的故事原就有过一些绚烂的浪漫色彩,经诗人冯至的手,加上了现代主义的诗情,尤其是意识流或内心情绪的渲染,就成了一个完整而透明的诗的果子。”这样赞赏一篇小说的“现代主义诗情”,在当时较为罕见。唐湜不仅在九叶派诗中看到了现代主义的倾向,还在七月派诗中也看到了现代主义倾向,唐湜将他们并称为“诗的新生代”,认为以穆旦、杜运燮为代表的诗人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艾略特与奥登、史班德们是他们的私淑者,而以绿原为代表的七月派诗人,由于私淑着鲁迅先生的尼采主义的精神风格,不自觉地也走向了诗的现代化的道路。
唐湜坚持现代主义立场,并把现代主义观念运用于文学批评之中。他的批评不仅填补了四十年代现代主义批评的空白,而且代表着四十年代现代主义批评的水准。就批评模式而言,唐湜继承的是李健吾式的印象批评,但又有所不同。印象批评强调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宣称“我所批评的只是我自己”;唐湜的批评中也有主观感受,但其志不在表现自己,而在贴近对象。由于具有丰富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实践以及由此带来的细腻的艺术感受能力,他的批评显得不“隔”,他能发现批评对象的长处,也能指出他们存在的问题。加以在批评时总是在作者的风格里沉潜观赏,往复漫游,便往往能把握对象的特征,入“心”三分。比如唐湜感受到穆旦“受难者的气质”,感受到陈敬容诗作中“男性气息与女性风格的融合”。这些感受都得到了研究界和批评对象的认同。他感受到杜运燮诗作意象丰富,但同时也发现作者对繁复题材处理“力不从心”,部分诗作显得“虎头蛇尾”。他对这些具体诗艺的探讨,是非常内行的。
虽然唐湜并未完全实现他在批评上的理想,但他通过文学批评,参与了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运作,发展了现代主义诗歌批评理论,在批评史上还是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唐湜先生和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祈、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穆旦九位诗人曾在80年代合出过影响深远的诗集《九叶集》,78年以后大家重新开始写诗,可穆旦已经去世了,在新时期主要是唐湜、杜运燮、辛笛、陈敬容、唐祈、郑敏6人继续发表创作,作为一班老人他们的诗仍然富有活力。而唐湜是创作产量最大的一位。
所以,他们是四十年代形成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而“九叶”这个说法是新时期才出现的,《九叶集》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册新诗的流派选集,在新中国文坛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有他们的地位。因为《九叶集》的缘故,他们九人后来被称作“九叶诗人”。 蓝棣之在《九叶派诗选》的前言中说到在中国语言当中“九”常常用来表示虚指很多或事物的丰富性,因此在这里的“九” 确制这九位诗人,也暗指四十年代也写现代主义或接近现代主义诗风的年轻诗人,这些人有马逢华、方宇晨、莫洛、羊?、李瑛、杨禾,甚至还有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校园诗人王佐良、汪曾祺等。说明他们的构成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
“九叶诗派”,其涵义除表明诗人的九数之外,是否还有他意?唐湜先生说,“九叶”即表示九人是诗坛上的九片绿叶而不是红花。